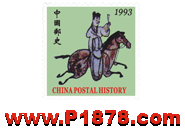以下是引用王厚邦在2008-9-15 21:07:03的发言:
石教授说:“我的观点是不必争论它们究竟是“戳号”还是“分、支局号”,可能戳号就是分、支局号,也可能不是”
我所以提出这问题,首先是石教授在这网上展出的他的邮集中他把北京小圆戳中(1)(2)(3)写为成支局号,这次看到严先生的书中也同样这么认为。而北京小圆戳是我感兴趣的研究课题。我一向认为是戳号,不是支局号。所以才有这争论。现在各持己见,严先生那边也听不到意见。将有待时日。
严先生书中专门研究了上海年位戳号,指出上海年位的2-26这些数字,是原来的工部书信馆邮佐,转业处理涉外信件发给他们的一人一戳,因此是戳号。但北京因不存在工部书信馆邮局,因此不是戳号而是支局号(一局一戳)。而我则认为:二者不必细分,反映在邮品上,都是经过了一道手续、盖上一个戳记,其编号是戳号还是支局号因此并不重要。实际上干支戳上的编号,同样存在是“戳号”还是“支局号”的问题。而此问题的解决,不是争论能够解决的,而且可能现代和清代规定完全不同(王先生也认识到这一点),所以我说可能戳号就是支局号,就是不是支局号又怎么样呢?还不是起着同样的作用——用以销票或用于中转。你管它究竟是一人一戳(在同一个局),还是一局一戳。就像一只烤鸭,鸭身上盖有记号表示经过“合格”检查,作为顾客没有必要去弄清楚此记号究竟出自哪个部门、还是出自何人之手。总之此戳记代表了该单位对此负责就是了。所以说争论此问题没什么大的意义。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-9-16 0:45:14编辑过] |